生命是什么?生物化学、物理学、哲学对生命本源的共同探索
1. 令人着迷的生命
地球表面布满了生命,而且通常很容易辨认。猫、胡萝卜、细菌都是活的,桥、肥皂泡、沙粒都是死的。但众所周知,生物学家们却没有关于生命的精确定义。因为生物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人们可能期望,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探索会在当代生物学和生物学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事实上,当今的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们并不讨论生命的本质。许多人认为生命的定义与当前的生物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Sober,1992;Taylor,1992)。当生物学家讨论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时,他们通常会把他们的讨论边缘化,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如今,生命的本质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操纵生命的经济产业在迅速增长。如基因工程、克隆和高速DNA测序等生物技术给我们以新的、前所未有的力量来重塑生命。最近的一项发展是,我们能够利用合成基因组学按照我们的规范重新设计生命(Gibbs,2004;Brent,2004)。在这一领域,Craig Venter 大力宣扬通过使用商业化的人造细胞来清洁环境或生产替代燃料,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Zimmer,2003)。目前通过在试管中合成最小人工细胞或原细胞的“湿”人工生命竞赛(Szostak,Bartel&Luisi,2001;Rasmussen等,2004;Luisi,2006;Rasmussen等,2007)也聚焦于生命本质问题。因为这场竞赛需要对生命的定义达成共识,这一定义需要超越我们所熟悉的生命形式。创造原细胞对社会和伦理造成的影响也需要我们对生命的本质有更深的理解。目前关于生命起源(Oparin, 1964;Crick, 1981;Shapiro, 1986;Eigen, 1992;Morowitz, 1992; Dyson, 1999;Luisi, 1998)和关于智能设计(Pennock, 2001)的争论更是如火如荼。
另外,一个名为“软”人工生命的最新进展也聚焦于生命本质的问题,它试图通过开发软件系统使其具有生命的本质属性(Bedau,2003a)。软人工生命创造了非常逼真的软件系统,有些人觉得它们真的是活的(Langton,1989a;Ray,1992),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计算机模拟是生命这一整套想法很荒谬(Patte,1989)。
此外,最近“硬”人工生命也取得成就,如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商用家庭真空吸尘器机器人Roomba(Brooks,2002),以及通过对自动化快速原型加以改进而设计制造的步行机器人(Lipson&Pollack,2000)。这些机器人的存在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仅由塑料、硅和钢制成的设备真的可以称为活着的吗?这些科学发展增加了如何精确划分生物的不确定性。
生物学对生命可以采取的形式加以概括,但这种概括也是基于真实存在的生命形式的。生物学家研究了大量不同的模式生物,如大肠杆菌(一种常见细菌)、秀丽隐杆线虫(一种线虫)和黑腹果蝇(一种果蝇)。选取尽可能不同的模式生物,由此可以最好地反映出生命可以采取的形式,对地球上的生物做出最为全面的概括。但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在地球上的。因此,对这些关于生命的概括目前取决于样本大小。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1998)曾经指出:人工生命有助于减轻这一问题。自然界中的生命有着惊人的多样性。但它们只是所有可能的生命形式中的一小部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都能使用软件、硬件或者湿件来合成一个可以展示生命核心属性的系统,我们就有大量的机会来扩展我们对于“生命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经验性理解。
哲学史上有三位伟人曾将关于生命的观点加以推进,而且这些观点仍然在当代的讨论中引起共鸣。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命是一种被如新陈代谢、感觉和运动等各个能力嵌套起来的统领者。这种被能力嵌套着的统领者就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或精神能力的概念,因此亚里士多德本质上把生命和心灵联系在一起。作为全面取代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中的一部分,笛卡尔认为生命只是一个复杂的但纯粹由物质机器执行的运作过程。笛卡尔认为,生命从本质上不同于心灵,他认为心灵是一种意识模式。笛卡尔在他的《人论》中勾勒了他关于生命的机械假设的细节。几代人之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努力将笛卡尔的唯物主义观点与生命独特的自主性和目的结合起来。
理解生命的本质并不简单。它需要对一些真实的且极其复杂的事物进行调查,而且这些事物具有巨大的潜在的足以改变地球面貌的创造性和力量(Margulis&Sagan,1995)。这项调查必然是跨学科的,它将审视那些多得惊人的关于生命的观点。比如整体性、内在稳定性、有目的性及可进化性,这些有趣而微妙的性质被视为刻画了生命的特征。但对生命的精确定义仍然难以捉摸,部分原因是病毒和孢子等临界的边缘情况,以及最近的人工生命的创造。更为复杂的是,生命在一系列哲学难题中处于中心位置,这些难题又涉及到重要的哲学问题,如涌现、计算和心灵。因此,可以预料得到,关于生命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运用了如功能主义等熟悉的哲学理论。另一些人则使用生化或遗传的解释与机制。还有一些人强调新陈代谢和进化等过程。关于生命的观点的多样性本身就很有趣并值得加以阐述。
2. 生命现象
生命具备很多特性及边缘案例,展现出许多谜题。本章的余下部分主要用来解释这些现象。
生命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所展现的特征和独特的标志。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特征对于生命而言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生命的典型特征。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生命特征的列表;例如,Maynard Smith, 1986; Farmer & Belin, 1992; Mayr, 1997; Gánti, 2000。但列表中的大多数特征基本上是重叠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清单上列出的特征也有明显的区别。一个很好的例子是Gánti(甘蒂)给出的特征(或者他称之为“标准”)。
Gánti 的特征分为两类:真实的(或绝对的)和潜在的。真实的生命标准规定了个体生命有机体作为生命存在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Gánti 在2003年提出的“真实的”生命标准如下:
(1)整体性
有机体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在不失去其基本属性的情况下,它不能被细分。如果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被分离并且不再相互作用了,那它不能被视为活着。
(2)新陈代谢
单个有机体从周围环境中吸收物质和能量,并使之发生化学反应。种子处于休眠状态时缺乏活跃的新陈代谢,但当外界条件重新激活其新陈代谢时可以称它们活过来了。基于这个原因,Gánti 将一般事物区分为四种状态:活着的、休眠的、死的或不可能活着的。
(3)内在稳定性
当生存环境不断变化时,有机体能够维持内部过程的稳定状态。通过改变和适应动态的外部环境,有机体保持其整体结构和组织。这涉及检测环境中的变化并对其引起的内部变化进行补偿,由此起到对整个内部组织的保护作用。
(4)有效的信息携带系统
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必须能够存储那些用于其成长和运作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可以被复制,通过繁殖而使子代继承得到这些信息。信息传递中发生的错误可以对这些遗传信息产生“变异”,而自然选择可以对由此产生的遗传变异进行筛选。
(5)灵活的控制
生物体内的过程是可控的,这使得生物得以持续存在并繁荣。这种控制涉及到一种适应的灵活性,通常可以随着经历的增加而改进。
对应这些“真实的”生命标准,Gánti 还提出了“潜在的”生命标准。一个单独的生命有机体无法展示出生命的潜在标准。潜在生命标准的决定性特征是,如果有足够多的有机体展示潜在标准,那么生命就可以在一个星球上繁衍生息并自我维持。对此,Gánti 提出了如下三点:
(1)生长与繁殖
年长的动物和不育的动植物都是活的生命,但没有一种能够繁殖。因此对于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言,繁殖能力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但由于个体有机体会死亡,只有当群体中的某些有机体进行繁殖的情况下,群体才能生存并得以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生长和繁殖是Gánti所说的“潜在的”生命标准,而不是“真实的”生命标准。
(2)可进化性
“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必须具有遗传变化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进化的能力,即在很长的一系列连续世代中产生越来越复杂和分化的形式”(Gánti,2003,pp.79)。由于随着时间推移而进化的并非是单个的生物体,而是这些生物体所属的种群,我们更应该说,生命系统是那些具有进化能力的种群的成员。究竟哪种生物种群具有产生更高复杂度和差异化的能力?这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死亡的必然性
生命系统会死。即便对那些通过克隆进行无性繁殖的生物体也是如此,不论是生命个体还是它的克隆体都要面对死亡。不存在不会死亡的永生系统,所以死亡是活的生物的属性。
Gánti 的生命标准和其他人的生命标准的清单总是反映和表达一些关于生命的先入之见。这似乎仍然无法回答生命是什么这一问题。每一个生命特征的列表都是由某些人通过某些标准将某些实例划入或划出而构建的。但这个标准又从何而来,我们如何确信它是正确的呢?如何可以让我们相信(符合列表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揭示出了生命的本质?因此可以看出,生命特征列表并没有给出关于生命是什么的最终回答。随着我们对生命了解的加深,我们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发展和成熟。因此,我们对于生命的特征清单也应当更进一步。
生命的另一个有趣特征是存在着一些边缘案例,这些案例介于有生命和无生命者之间。常见的例子如病毒和朊病毒,即便没有独立的新陈代谢,它们仍然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和传播。休眠种子或孢子是另一种边缘案例,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比如那些被冷冻的细菌或昆虫。也存在一些明显不是生命的案例,但它们却仍然具有生命系统的特征。不会有人认为蜡烛的火焰是生命,但其组成分子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外形,这一过程有些像新陈代谢(Maynard Smith,1986)。可以生长和增殖的微小的黏土晶体群是另外一个边缘案例,特别是因为它们可以在适当的环境下进行自然选择(Bedau,1991)。一场正在蔓延(“增殖”?)的森林大火也是这样一个边缘案例,在大火的边缘处,火势从一棵树传递到另一棵树,就好像细菌种群在边缘处的成长。还有更进一步的由一群有机生物构成的超有机体这样的边缘案例,比如完全群居的昆虫群落,其功能类似于一个单独的有机体生命。虽然这存在争议,但生物学家们认为超有机体自身会视自己为活的生命。另外一种边缘案例还包括如Tierra这样的软人工生命创造物。Tierra是一种软件,它创建了一个自发进化的计算机程序群,这些程序在计算机内存中繁殖、变异和进化。Tierra的发明者认为Tierra是真实活着的(Ray,1992)。这将彻底颠覆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生命的一般概念。最后一类边缘案例是身边的那些复杂适应系统,比如金融市场或万维网。上述案例呈现出生命的大量特征,因此一些人认为,最为简单的也是能将生命现象的全部范围给出最统一的解释就是:将这些自然的复杂适应系统视为真正的生命(Bedau, 1996, 1998)。

3. 生命之谜
第三点是生命本身存在很多谜团。我们将罗列如下六点。任何关于生命的描述都应能解释这些谜题的起源;更重要的是,这些描述应该能解决这些谜题。有些谜题可能仅仅是出于困惑,但另一些则是自然界中基本而令人着迷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1)起源
生命是如何从非生命中诞生的?生物学又是如何从纯化学中演变来的?考虑一个只经历化学反应的系统,其中的化学反应持续改变着化学物质的浓度,这样的系统和一个包含生命的系统有什么不同?生命现象和单纯的物理化学现象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两者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在原则上和实践中得以自然地跨越?丹尼特(Dennett)认为,达尔文的解释方案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方案通过引入“有限的退化,其中所寻求的非凡的特性(即生命)是通过轻微的,甚至是不可察觉的修正或增加而获得的”(1995,pp.200)。
(2)涌现
生命是如何出现的?属性B依赖于属性A而产生,并且在产生后独立于属性A,具有自主性,则称属性B是从属性A中涌现出来的。不同类型的依赖和自主独立将产生不同程度的涌现(Bedau,2003b)。如果涌现现象牵涉到原则上不可再分的自上而下的因果力量,则称之为“强”涌现。心灵哲学中的知觉或感受的特性就是一个例子(Kim,1999)。如果A和B是同时,则B从A的涌现是共时的。这涉及到某一时刻有哪些属性存在。这些属性可能正在发生变化,但在某一瞬间的属性A和B之间的关系是这些属性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的一个静态快照。相反,如果属性A先于属性B发生,并且属性B在属性A产生后就产生了,那么属性B从属性A的出现是动态的。生命是一种动态形式的“弱”涌现的范例,除非观察它们产生的过程,或观察其模拟,它涉及到的那些宏观属性都是不可预测或不显著的(Bedau,1997,2003b)。
(3)层次结构
生命对外表征为多种多样的结构层次。每个有机体相对于其内部的有机组织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不同种类的有机体组织之间存在的相对复杂性,由此而形成了另一个层次结构。最简单的有机组织是原核细胞,它们的成分相对简单。比较复杂一些的是含有复杂细胞器和细胞核的真核细胞。多细胞有机体更为复杂;它们的组成单元(单个细胞)也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例如,它们可以自己保持生物活性)。此外,哺乳动物有复杂的内部器官(如心脏),当一个哺乳动物死亡时,这些器官可以被采摘下来并保持其生物活性,然后通过外科手术植入另一个哺乳动物体内。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生命倾向于产生并包含这样的层次结构?这个问题既适用于所有生物体共同组成的复杂层次结构,也适用于每个生物体内部组织间的层次结构。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提出下一个问题。有机体是典型的有生命的范例,但我们也将器官和单个细胞称为有生命的。例如,细胞凋亡是生物体内活细胞程序性死亡的一个重要过程,医院努力使某些器官在人死后仍能存活,以便可以移植到其他人体内。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哺乳动物、它的心脏和组成心脏的细胞是否在相同意义上活着。
(4)连续度
生命有程度之分吗?生命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布尔属性,还是一个带有过渡的灰色地带的连续属性?常识倾向于布尔的观点:兔子是活的,石头不是,讨论到此结束。但也有一些像病毒这样的边缘案例,如没有宿主,就无法实现复制。孢子或冷冻细菌可以保持休眠状态,并且长期保持不变,但当条件变得有利时,它们又会复活。那病毒和孢子是完整意义上的生命吗?进一步说,当原始生命从前生物的化学汤中涌现出来时,它们与非生命的前辈们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一些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是连续的(例如,Cairns-Smith, 1985; Emmeche, 1994; Dennett, 1995)。另一种选择是接受生命和非生命之间存在的明显区别,但允许一小步就可以跨越它。两者之间有四种区分:(i)无生命且永远无法具有生命活性的东西,(ii)正在存活的东西,(iii)已死亡但曾经活过的东西,或(iv)处于休眠之中但能够再次具备生物活性的东西。这些区分方案有助于解释一些边界案例的存在,并将它们重新分类(例如,种子和孢子正处于休眠状态而没有体现出生命活性的情况)。但这并没有完全解决生命现象连续的谜团,因为这四种区分中也存在着边缘案例,例如介乎生死之间的情况。
(5)强大的人工生命
基于软件和硬件的人工生命给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计算机创造物是否真的可以是活着的?(Langton,1989a;Patte,1989;Sober,1992;Emmeche,1992;Olson,1997)一方面,某些独特的碳基大分子在所有已知生命体的生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许多人工生命似乎都假定生命可以在经过适当编程的计算机中实现。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区分。第一个是哲学上有争议的问题——凭什么说计算机或机器人是活着的。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的技术问题是,是否有可能通过建立一套软件系统或硬件设备(例如机器人),使得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真正活的。这里的挑战是,我们是否能够真的理解如何通过适当的原材料来实现生命的过程。这个基于软件的“强”人工生命坚信人工生命软件的实例是真的活物。对于基于硬件设备的“硬”人工生命和基于实验室设备的“湿”人工生命,人们也有类似的强硬立场。这些强硬的立场对比于那些无争议的“软弱”立场,让人们相信通过计算机模型、硬件结构和湿实验室造物可以进一步理解生命系统。而且,湿人工生命的强版本在直觉上是看起来很合理;我们内心通常愿意接受那些在实验室里从零开始合成的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因此,关于强人工生命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软人工生命和硬人工生命上。
(6)心灵
另一个谜题是,生命和心灵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联系。例如,植物、细菌、昆虫和哺乳动物对环境具有各种敏感性,这种环境敏感性以各种方式影响它们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交流形式(例如,Dennett,1997)。这些都是智能行为的形式,这些“心智”能力的相对成熟似乎与这些生命形式的相对成熟度相对应,并对它们给出了解释。因此人们自然会问,生命与心灵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当然,进化过程给出了生命和心灵之间的系谱联系,但是如果 Beer(比尔)所说的“这是一种适应行为,一种……用来应对我们所在的复杂的、动态的、不可预测的世界的能力,事实上,这是[智能本身]的基础”,那么生命与心灵之间的联系将更加深刻(Beer, 1990, pp.11; 另见 Maturana & Varela, 1987; Godfrey-Smith, 1994; Clark, 1997)。由于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应对一个复杂、动态且不可预测的世界,也许这种适应性的灵活将生命和心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4. 对生命的解释
人们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尝试来描述所有生命的普遍特征。在本节中,我将讨论几种对生命的主要解释,指出它们的动机、优势和劣势。我还将指出一些认为这些解释无用的怀疑立场。
首先考虑生命本质与生物学无关的怀疑立场(Sober, 1992; Taylor, 1992)。这种怀疑论产生的原因是:不论生命是否能够被充分定义,不论哪种关于生命的观点最终获胜,生物学家们都能继续他们的生物学研究。然而,必须承认,最近的发展,如试图从零起步制造最小的人工细胞,确实需要科学家们开始去确定什么才是生命的本质,即使这些观点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因此,这一问题即便曾经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现在也不再是这样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至少有关于生命的最小充分条件的可行假设时,才能开始着手构造一个最小形式的生命。否则他都不知道该去做什么。
怀疑论的第二种形式是认为生命不存在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加以认定,而只是由一组具有Wittgenstinian(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的事物组成。不同形式的生命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或特征,但对每一个群体中的单个个体的性质而言都有例外。这些性质通常由活生物体所拥有,但它们不是严格必要或充分的。Farmer和Belin列出了八个特征:过程;自我繁殖;自我表征的信息存储;新陈代谢;与环境的功能互动;各部分的相互依存;扰动下的稳定性;以及群体中的成员具有进化能力。然后,他们解释说,当他们对试图找到比这个特征列表更精确的东西感到绝望的时候,生命的集簇概念(cluster conception)诞生了。
似乎没有一种单一的属性能够标记生命。我们赋予生命的任何属性要么过于宽泛,以致于许多非生命系统也具有这类特征;要么过于具体,以致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满足这类具体特征的反例,但从直觉上判断这个反例却是活着的。(Farmer&Belin,1992,pp.818;参见Taylor,1992)
集簇概念相当于对存在统一生命理论可能性的怀疑。
集簇概念的一个优点是,它为边界案例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解释。所有集簇概念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边界案例。集簇概念的一个特点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生命形式是由一组特征而不是另一组特征统一起来的。集簇的观点必须只接受给定的特征,然后用这些特征来标识集簇。正因如此,这种观点只能在事后确定生命的特征;它无法预测或解释这些特征。那些认为应该对生命特征做出解释的人们会发现集簇概念并不令他们满意。
另一种类似的怀疑论观点质疑生命是天然的这一想法。Keller(2002)说,生命是一种人为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天然的概念,也就是说,是我们(人为)给出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区别,而不是自然给出的。这可以对那些边缘案例给出解释。由于生命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人们应该期待它的边界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边缘案例。这一观点还为对抗那些生命之谜提供了一些通用的反驳说辞,因为可以预料的是,一个易变的人造物自然会产生那些谜团。Keller 关于生命是人为观念的论点表明,目前关于生命有本质的假设是200年前才出现的,对生命本质的探索是由从非生命中创造生命的尝试推动的(这往往会打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科学和技术进步产生的新概念违反了旧的分类方法,如生命/非生命的区别(Keller,2002)。
所有这些争论都存在问题。首先,所有现代科学概念,如物质和能量,都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产生的,并从那时起不断发展。因此没有一个偶然的、可追溯的最近起源表明某个类是人工类,除非一下子在所有的科学概念中做到这一点。第二,在实验室中搭建从非生物到生物之间的桥梁不需要消除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如制造第一架飞机不会消除飞行和非飞行之间的区别一样。需要记住的是,我们是在寻找生命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当前的生命概念。
现在,对于“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简单地给出一个生物的分类系统。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当于要求给地球上所有活着的生命列出一个详尽的清单。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但却充满了偶然性。这个分类系统将无法给出那些可能存在却并未发现存在迹象的生命。这说明了分类学观点的沙文主义,即假设我们所知的生命已经穷尽了所有生命形式。像存在于欧罗巴(木卫二)这样的地球以外的不相关的生命形式是不列在所有这样的分类系统中的。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随时调整我们的分类系统,这是我们的学习方式。
有些人给出了生命的生化定义。考虑到物理和化学的一般约束条件,他们试图具体说明任何形式的生命必须具备的生化特性(Pace,2001;Benner,Ricardo&Carrigan,2004)。这包括热力学极限、能量极限、物质极限,甚至地理极限。生化定义中的生命特征有时被称为生命的生化“共性”,该定义总是以关于生命的先验描述为前提;它陈述了任何生化系统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可能性,以满足先前对生命的描述。Pace(2001)和Benner等人(2004)关于生命的生化定义是基于进化给出的,因此Pace和Benner专注于遗传能力的生化共性,并强调DNA等分子可以在世代之间存储和传递信息。生化定义通常是目光短浅的,并假定所有可能的生命形式都与熟悉的生命形式相似。人们可以想象,从一个不同于基于进化,如基于新陈代谢的生命概念开始,到最后强调不同于DNA遗传信息(如使开放系统在热力学第二定律情况下仍能保持其结构)的生化共性。
生化生命定义的一个遗传学实例是,Venter 将生命定义为足以维持其存在的最小基因组(Hutchison et al.,1999)。该观点继承了生化定义的局限性。基因组定义了包含足以维持生命的最简单的已知基因组。但它并没有包含每种生命形式中的基因,因为通过不同的基因可以实现相同的基本生命功能。许多人会质疑分子定义对遗传特性的局限性,因为生命核心所涉及的远不止基因(Cho et al., 1999)。
那些从零开始制造人工细胞或“原细胞”的科学家们都承认,生命的本质是有争议的,但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构建一个可以进行新陈代谢和进化的独立系统(例如,Rasmussen等人,2004)。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在化学层面上整合如下三个过程的化学系统都可被视为一个人工细胞 。首先是组装某种容器(如脂质囊泡)并在其中生存的过程。其次是修复和再生容器及其内部包含物,使整个系统得以维持的新陈代谢过程。这些化学过程由第三个化学过程形成和引导,该过程涉及对该系统的信息(“基因”)编码并在系统内部加以存储;当这些信息被复制时可能会发生错误(“突变”),因此系统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这种三位一体的生命视角需要容纳、新陈代谢及进化这三种化学过程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三者之间功能上的反馈。这种将原细胞生命视为一个完整的功能三元组的观点将任何一个完整包含这三种过程的生化实现都视作真正的生命。
上一代的心灵哲学一直被功能主义所主导:他们认为心灵是一种特定的输入输出装置,拥有心灵只是拥有一组内部状态,它们彼此之间发生因果交互(或“执行功能”)、对环境的输入也发生因果交互(或“执行功能”)并且以特定的方式向环境进行输出。功能主义关于生命持有类似这样的观点,即一种执行着特定相互作用过程的网络实现。某些(如信息处理、代谢、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运行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内;其他(如自我繁殖和适应性进化)过程的运行要经历许多代的生物体。这些过程总是通过某些具体的底层物质实现的,但只要过程的形式得以保留,过程具体由哪种底层物质实现的其实无关紧要。基于这些原因,对于生命来说功能主义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Chris Langton 对人工生命的辩护是功能主义关于生命的经典陈述:
生命是形式的属性,而非物质的属性,是物质组织的结果,而非物质本身固有的东西。(Langton, 1989a,pp.41)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一个组织得当的人工原始集合,在自然生命系统中扮演着与生物分子相同的功能角色,与自然生物一样地承担着“活着”这一过程。因此,人工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它与地球上进化出的生命相比,只是由不同的物质组成。(Langton,1989a,pp.33)
我们可能不确定定义生命过程的细节,我们可能希望保留人工生命创造物是否真的存在的判断。然而,很难否认 Langton 的观点,即生命的特征过程,如新陈代谢、信息处理和自我繁殖,可以在广泛且潜在的开放性材料范围内实现。因此,关于生命的某种功能主义的前景似乎更为光明。
功能主义在心灵方面的主要挑战是与意识和感受质(qualia )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生命的功能主义并不面临任何类似的问题。功能主义在心灵方面的另一个挑战是解释人们的心灵状态是如何有意义的或具有语义内容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许多以进化的生命形式结构而实现的生物学功能给出了一个自然主义的解释。这种生物功能为生物的内部状态赋予了一种意义或语义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生物为了获取营养而试图寻找食物。许多哲学家乐观地认为,功能主义中关于精神的意义问题将通过类似达尔文的关于精神状态的生物学功能的解释来加以解决(例如,Dennett, 1995)。
另一个与生命相关的功能主义的明显威胁是,从某种相关的意义上来说,生命中涉及的过程是不可篡改的或非计算的(例如,Emmeche, 1992)。Bedau (1999) 认为,生命表面上的非计算性是可以解释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过突变产生的优势性状往往会持续存在并在群体中传播。此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种群中的性状重复率将以这样的倾向方式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通常对种群有利的方式。这些性状重复率的动态模式是从自然选择、突变、漂移等微观层面的偶然事件中以统计模式出现的。Bedau认为这些模式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柔韧性。这种性状重复率的模式不是那种精确的、无例外的普遍总结,而是只在大多数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成立。此外,那些模式规则也存在例外,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样一个法则”,即它们(这些模式规则)也不过是为了实现某种更深层的适应目标而给出的副产品。例如,Bedau描述了一个突变率可以进化的系统,并表明这种倾向于进化的突变率将使种群的基因库保持在“无序边缘”;但这种规律性也存在例外,这是由于运作突变率进化的更深层规律是(通过突变率)以最佳方式平衡进化中的“(对本体的)记录”和“(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创造”(详情见Bedau,1999)。在这种情况下,柔韧的规则反映了(生命存在)一种潜在的能力,即能够在开放的环境变化中做出适当的反应。尽管生命能以适当的计算机模式进行模拟,这仍然展示出生命过程存在一种不可篡改性。
功能主义没能确切回答在生命的功能表征中这些过程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基于薛定谔的影响,生命的定义过程是通过新陈代谢来对抗热力学第二定律:
什么时候说一个东西是活着的?比起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而言,有生命的物质能够在比我们期待的更长时间里持续地“做某事”、移动、与周围环境交换材料等等。一个有机体显得如此神秘,正是由于它避免了快速衰变到丧失活力的“平衡”状态:活着的有机体是如何避免这种衰变的呢?显而易见的答案是:通过吃、喝、呼吸和(就植物而言)消化。技术术语是新陈代谢。(Schr?dinger, 1969,pp.74-6)
以新陈代谢为中心的生命观吸引了许多人(Margulis & Sagan, 1995; Boden, 1999)。它们与关注自创生的观点密切相关(Varela, Maturana, & Uribe, 1974; Maturana & Varela, 1987)。
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核心过程的观点有一些明显的优势,比如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直觉上认为晶体不是活着的(只有在晶体的边缘存在一些分子的代谢流,而在晶体内部并不存在)。此外,需要通过新陈代谢来对抗熵增这一事实意味着,新陈代谢至少是所有物理生命形式的必要条件。新陈代谢也很自然地解释了无生命的、活着的、死亡的和休眠这四者之间的区别。无生命体原则上不能代谢,而那些活着的生命体正在代谢。那些死亡的曾经活过并且新陈代谢过,而如今正在腐烂。休眠的曾经活着但当前并不进行新陈代谢,而如果环境合适,它们就可以再次进行新陈代谢。
将新陈代谢作为一种对生命的全面描述的主要缺点是,许多新陈代谢实体直觉上似乎并不是活着的,或者不以任何方式与生命有关。典型的例子包括蜡烛火焰、涡漩和对流胞(Maynard Smith,1986;Bagley&Farmer,1992)。这些例子本身并不能决定性地证明新陈代谢对定义生命而言是不充分的,因为先于理论的直觉判断可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平衡代谢是否充分解释了生命的特征,并解决了生命的谜团。
一些人认为,所有生命的核心特征是开放式的适应进化过程。其核心思想是,可以区分生命的是其开放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动和适当地适应环境中不可预测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的独特之处在于,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通过新的、智能的策略以自动的方式适应性进化以生存和繁荣。Maynard Smith(1975,pp.96f;另见Mayr, 1982;Cairns-Smith, 1985)简洁地解释了生命的关键取决于适应的进化过程这一观点的正当性:
我们将把任何具有繁殖、遗传和变异特性的实体种群视为活着的。这一定义的正当性如下:任何具有这些特性的种群都将通过自然选择进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其环境。如果时间充足,自然选择可以产生任何程度的适应性复杂性。
这些评论说明了适应性进化的过程如何解释了生命的特征、边缘案例和谜团(见Bedau, 1998)。
对于以进化为中心的观点,有一些典型的批评。其中一个反例是作为活着的但不能生育的生物(如骡子、老人等)是不能参与进化过程的。典型的回应是要求生物体是应通过进化过程产生,但并不要求它们一定能影响进一步的进化。另一种所谓的反例是一个显然非生命的系统,如粘土微晶的种群或自由市场经济,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些反直觉的例子,因为以进化为中心的观点对生命的特征、边缘案例和谜团提供了如此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Bedau,1998)。
并非所有的立场都是相互对立的,很多都彼此一致。例如,功能主义与原始细胞整合三元组对最小生命的解释是一致的。此外,对生命本质的描述都涉及到生命的生化特征,许多关于生命的描述是重叠的。理解生命的问题在于确定这些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
5. 理解生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比较和评估对生命本质的描述?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看看每一种理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有多好。这相当于做三件事:解释生命的特征,解释边缘案例,解决生命的谜团。理解生命的问题就是解释这三件事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初的一个困难是混淆了问题的关键。一些研究认为,对生命的任何解释的关键检验,是使其符合我们的前理论直觉,即哪些事物是活的,哪些事物不是(例如,Boden, 1999)。但有应该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直觉。一个好的生命的理论可能会使我们对生命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这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哪些情况下存在生命的态度。因此,尽管我们的前理论直觉有一定的分量,但它们并非是不可侵犯的。
也可以问一下“生命”这个词在今天英语中的含义。但关于“生命”一词相关的刻板印象是习以为常的,反映了我们当前对生命这一情景的最低的共同印象。因此,我们不太可能依靠单词“生命”的含义来了解生命。
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对生命一词的概念进行分析而学到很多东西。正如“生命”的意义一样,我们当前的生命概念将反映我们当前对生命的理解。如果我们想了解具有生命特征、边缘案例和生命谜团的现象的真实本质,我们应该从自然现象本身去研究,而不是我们的单词或概念。我们应该期待我们对生命现象的理解能够不断发展与推进。
解释生命现象至少涉及对生命根源或本质的粗略观点,也许还包含关于生命的粗略定义。源于Kripke(1980)的科学本质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认为如水和黄金等自然类的本质是其由经验科学发现的潜在因果力量(见Bealer,1987)。水和黄金等物质的本质是它们表面之下的化学成分。另一方面,生命是一种柔韧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化学物质。因此,与水或黄金不同,生命的本质可能包含于解释其特有因果能力的(如新陈代谢、繁衍和感觉)过程的特征网络。在这方面,生命更像是热,这种物质中的特定过程(高分子动能)。特定温度(比如23°C)是一种特定的过程,可以发生在所有物质中。生命也是一种过程,可以发生在不同种类的物质中,但与温度不同的是,并非所有种类的物质都可以是活的。综上所述,将生化约束映射到可以实例化生命的物质种类上,这就产生了生命的生化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代科学对生命是什么没有达成共识,关于生命的科学本质主义可能是正确的。科学本质主义是关于生命本质的发现方法的哲学观点,而不是关于生命本质具体是什么的观点。可能需要等待进一步的科学进展才能从细节上给出生命的科学本质论定义。
目前尚不清楚生物是否具有使其本质上成为生命的特征。例如,在 Dennett 看来,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是一个程度问题,生命太“有趣”了,因此无法寻求其本质(1995,pp.201)。事实上,当代生物学和生物哲学完全信奉达尔文式的反本质主义,即物种没有本质,其成员没有必要和充分的属性。相反,物种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只是统计意义上的。物种只不过是抽象的可能特征空间中的一团云或一丛草。尽管可能的特征空间的某些子区域由于不适应而未被占用,但究竟哪个可接受的子区域被占用是一个偶然性事件。没有哪个子区域比任何其他区域更本质;在固定不变的柏拉图本质面前,每个子区域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概括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被生命的集簇概念所吸引,因为这似乎是反本质主义的直接结果。
达尔文的反本质主义是针对一个狭隘的本质概念的,这个概念推崇那种无例外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排除了边缘案例。边缘案例是生命的标志之一,因此生命的本质必须足够广泛和灵活,以包含边缘案例。人们可以接受达尔文的反本质主义的同时仍然接受关于生命的科学本质主义。在这种观点下,生命的“本质”将是解释生命现象的任何过程,包括生命的特征、边缘案例和谜团。生命不是由无例外的限制条件来定义的,而是由经验来定义的。不幸的是,当代哲学术语模糊了达尔文的反本质主义和科学本质主义在生命问题上的相容性。
Clelland 和 Chyba(2002)认为现在给生命一个规范的定义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目前对生命的理解太有限。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等到科学家们能够区分出更多种生命的形式时,再对生命给出规范的定义。然而,现在我们可能正处在这样的一个需要构建关于生命现象的试探性和可测试性假设的时机。这些假设很有可能是错的,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理论(Wimsatt, 1987)。当我们手头有了好的生命理论,就可以提炼出隐含在它们中的生命的定义。因此,对生命定义的追求,更像是对生命本质的追求。
生命是自然界中最基本且最复杂的现象之一。因此,关于生命的解释既丰富又有趣,具有复杂的结构。这些解释有多种形式,如怀疑论、详细的生化和分子描述,以及抽象的功能主义,并且它们强调了如新陈代谢和进化等基本的生物学过程。评估这些解释的标准包括,它们解释生命的特征、边缘案例及解决生命之谜的能力。许多关于生命的主要解释仍然缺乏实质性的发展和对其中多个方面的仔细评估。因此,理解生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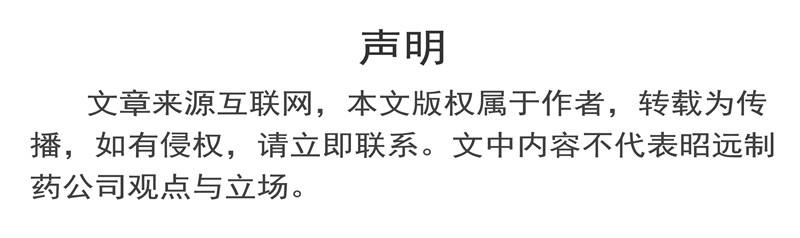
- 上一篇:“免疫”的社会内涵:疫苗为谁而打?
- 下一篇:基于县域官员饮酒行为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