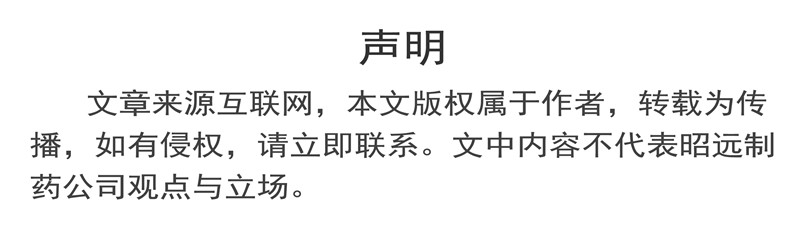“免疫”的社会内涵:疫苗为谁而打?
疫情进入持久战,是时候重新理解“免疫”的社会内核了。
那天晚上,我忽然开始有点流鼻涕。一边鼻子堵住了,我开始张口呼吸,嗓子干痒得难受。身体上传来的任何一个信号——不管是丝毫的肌肉酸痛,还是任何一个喷嚏和咳嗽的冲动,都让我十分不安。
该不会是感染了新冠吧?
一夜未睡安稳的我,脑中一直回想着这两周生活轨迹中可能被感染的——到底是讨论课的课堂,还是点单的饭馆?是徒步的时候和没戴口罩的大叔聊天,还是久违了的同学一起喝的咖啡?第二天一早我急忙跑去最近的诊所,快速测试(Antigen Test)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是阴性,我的心放下了大半。医生询问了我的症状,推断是鼻炎,后鼻滴涕(postnasal drip)导致的喉痛、咳嗽,开了鼻喷剂,药到症除。(当然,保险起见,也在家等了核酸结果。)
对于打过疫苗的我而言,即使出现突破性感染,症状也很轻,对于没有基础病的年轻人而言,只有极小的概率会发展成为重症,几乎不可能导致死亡。说实话,过敏性鼻炎和新冠于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都仅仅是不舒服几天,耗掉几大包面纸罢了。让我强烈不安的,是病毒围绕我的展开——我过去两周内所打过照面,甚至长谈、共进午餐的人,他们究竟会如何?那些即将和我见面的人,对我又会抱有怎样的担忧?他们是否接种、是否安全,我不得而知;而“我”作为一个博士生、一个助教的角色,和我作为一个可能影响到身边人的潜在的传播者的角色,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新冠对个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诊疗结果;对社会,亦不仅仅是一个确诊数字——而是参与其中的每个人如何理解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跌跌撞撞中前行的“后疫情社会”中,“个人”尤其显得脆弱无力。“打疫苗、勤洗手、戴口罩、不聚集”这些不断重复的针对个人的卫生规训,根本无法消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焦虑。
如果说2020年的疫情,还是社会管理者的策略之争,那么2021年疫苗问世之后的疫情,就成为了社会与个人的角力。在疫情短期内无法消散的当下,个人如何消化关于疫情的社会关系?社会又如何处理个人对于责任和风险的理解?疫苗与口罩,究竟是个人的风险权衡,还是社会共抗病魔的长城?疫苗究竟为谁而打、口罩为谁而戴?
“群体免疫”的迷思
早在新冠之前,美国作家尤拉·比斯(Eula Biss)就在《免疫》中深刻地探讨了这些关键问题。比起从上至下的医学科学视角,比斯的这本书从一个新生儿的母亲的角度出发,带着些许初为人母的焦虑,自下而上地梳理了免疫和疫苗这个从根本上就扎根于社会土壤的概念。
比如,“群体免疫”这个从疫情一开始就被反复提及的概念。在流行病学家那里,这不过是一个科学术语,描写了当一个群体特定比例的人群获得免疫力时,病毒便会自动消亡。然而,在不负责任的政客嘴里,群体免疫被误读成为了一种“躺平”的方式,混淆了免疫的目标与途径。
但尤拉·比斯指出,群体免疫一词的关键,是“群体”。接种不仅仅影响单独的个体,还同时影响着一个“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人群接种疫苗,是在构建一个“免疫力银行”,或者献血的血库。每一个人对这个银行做的贡献,都可以被用于那些不能或者未能被他们自身免疫力保护的个体们。疫苗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接种,也没有一种疫苗是百分百有效的。但是,当一个群体中大部分的人拥有免疫力,就能够大大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把未接种的人保护起来,这才是疫苗真正的“保护力”。在新冠流行的地方,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感染的因素,不仅是自己有没有打疫苗,还有自己身处的社区接种率如何。
然而,群体免疫在个体身上很难体察。我打了疫苗,没得病,疫苗是有用还是没用呢?我是愿意承担疫苗所带来的极小的风险以及副作用,将我自己的免疫“捐”出给社会,还是心里打好小算盘,搭群体免疫的“便车”?面对传染力越强的病原体,就需要越多的人“捐”出免疫。
但在当下,个体的叙事,占据了生老病死的绝大部分篇幅,也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势,而在对疾病与社会关系的诠释中,这种思维的作用,比单纯的“事实”更加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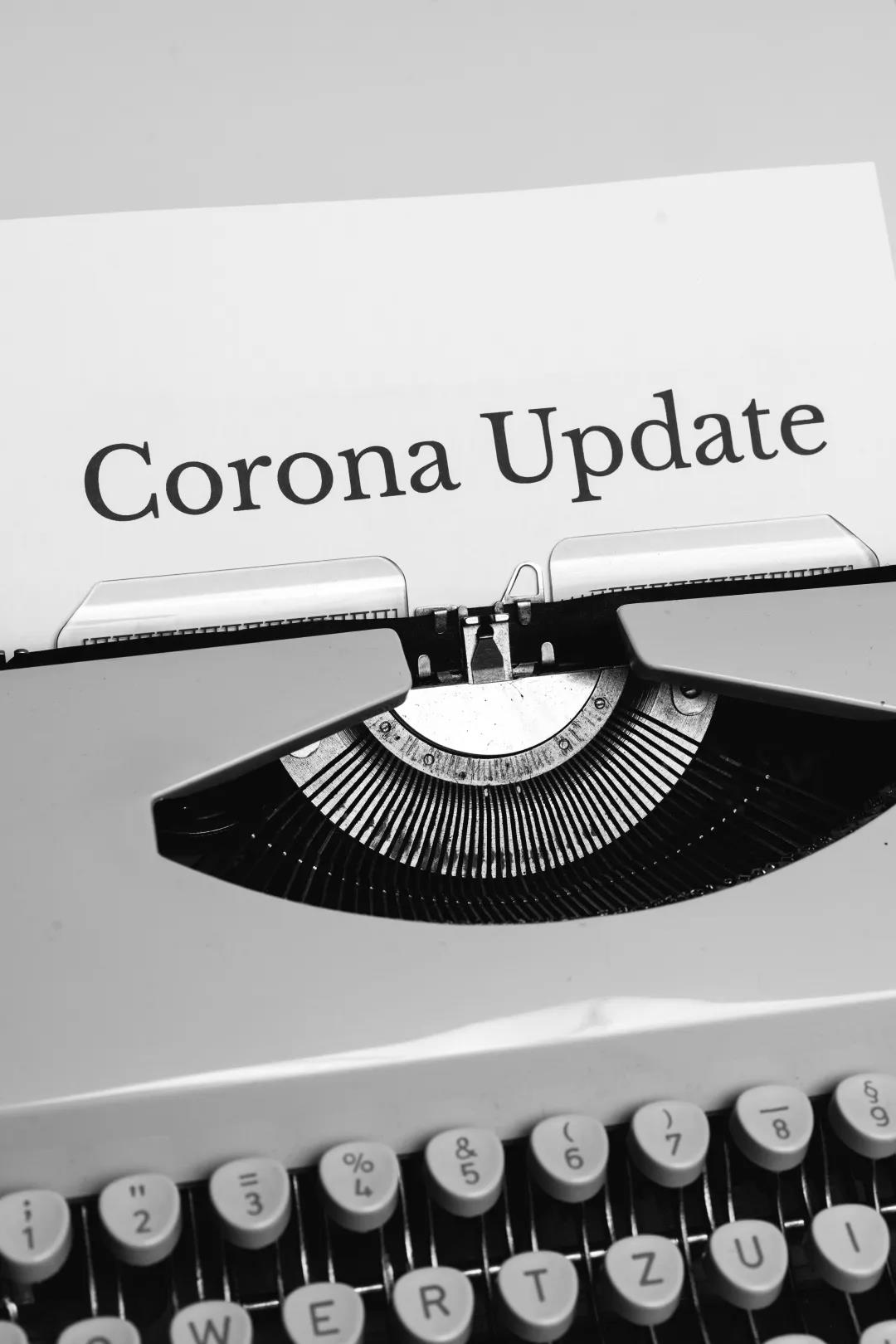
健康不是“个人”的事
比斯在《免疫》中写道,“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这个词,通常让人们联想到牲畜群(herd),若不是盲目随大流,就是被更高的力量所掌控,这不是什么让人信服的词汇。而在现代社会,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用自我的方式在思考、计算,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独立照料的家园”。
这种思维也不仅是自己,还有属于自己的家庭。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教授珍妮弗·莱奇(Jennifer Reich)在深入研究了一群拒绝为自己的小孩接种疫苗的母亲后发现,这些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仅仅看作是自己养育的作品,对群体的健康态度淡漠。她们用自己的“照料”将小孩的身体层层包裹,并对疫苗这种“外来”的东西持有巨大的怀疑。比起真正的“反科学”,这种个体化的叙事无疑更加深刻地扎根于现代人的健康观中。
医疗的个体化,也并不仅仅是观念问题。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医疗卫生体系也更倾向于向个体提供服务,而忽视了社区的、群体的健康。这一点在美国社会体现得特别明显,医疗极度市场化、医疗方面贫富差距的鸿沟、政府对医疗体系的放任,都使健康逐渐成为了一种个人的特权,并将面对病痛的个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也种下了不信任的恶果。
《免疫》一书中写道,许多人对疫苗抱有敌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疫苗是大药企、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阴谋。“资本主义禁锢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难以设想竟会有一种公益精神能与资本争锋,即使这种精神是以人类生命的内在价值为基础,”比斯写道,“……在我们当中竟然有这么多人宁愿相信,全世界整个医疗系统的研究人员、卫生官员以及医生都会愿意为了钱财私利去伤害儿童——这才是资本主义真正从我们身上掠走的东西。”
在疫情袭来时,一个缺乏健康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从上到下都只能陷入混乱,或者说是无助——只能一遍遍重复关于“一个人该不该戴口罩”的争议。很少有人关心个体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疾病境遇,一个必须要天天出门乘坐地铁前往曼哈顿市中心工作的服务业者,应该如何应对每日来往的人流;或者在美墨边境只说西班牙语的老人,应该如何理解疫苗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影响着他们做选择的能力,而他们自己的健康和周边人的健康,又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身体的健康,从来都依赖于其他人所做出的选择。”比斯写道。或许,我们现在的社会离传染病肆虐的年代已经过去太远,而当新的传染病出现时,我们对于疾病和健康的理解,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
互信的社会才能向前走
隐喻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如果有人将自己的身体比作私有的花园,不容得任何外来的势力“插手”,那么就有人会将任何危险的事物视作闯入自己家园的威胁。面对不可知的风险,人们的理性难以以量化的方式驾驭,而不可量化的恐惧,则是驱动我们愤怒、怀疑与抵抗的原因。这种恐惧的来源,不仅仅是病毒本身,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其中也不乏偏见和歧视。
凯瑟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从疫情以来一直收集美国国内各种人对疫情议题的反应。在德尔塔毒株肆虐的时候,一个问卷是“谁应该为此负责”。接种过疫苗的人,将矛头指向未接种疫苗的人;而未接种疫苗的人,则将矛头指向了“带来病毒的外国人”。这让我想起,去年疫情在欧美暴发的时候,回国的人、特别是留学生被指“千里投毒”,而不去想象这些“外人”本也是受感染的病人。
外来与本地;洁净与肮脏;疫情的战争与抵御疫情的长城,等等等等,都隐含了一种二元的隐喻。然而,疾病从来都不是二元的结果。人类已经与各种各样的病原体从史前一直战斗到现在,甚至形塑了我们的肉身和社会。问题不在于谁该为疾病的流行而负责,而是一个真正互信、互利的社会,如何一起在一波又一波的流行病侵袭下,生存下来,如何在商讨中平衡各方的利益,如何在基本的认识上达成一致。而互信不仅仅是相信决策者,而是相信其他的个体都有保护群体的意愿,相信人们自由做出的选择带有善意的考量。
一场大流行,是一个社会信任程度的试金石,更是我们重新思考疾病、个人与社会的契机。在这条路上,每个社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资料:
尤拉·比斯,《免疫》,彭茂宇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ich, J. A. (2014). Neoliberal mothering and vaccine refusal: Imagined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privilege of choice. Gender & Society, 28(5), 679-704.
https://www.kff.org/coronavirus-covid-19/